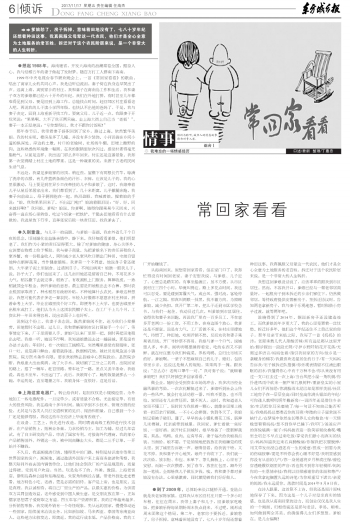●想起1988年,海南建省,开发大海南的浪潮席卷全国,振奋人心,我与结婚五年的妻子做起了发财梦,随百万打工人群南下海南。
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唱出了离家儿女的共同心声,我是边听边流泪,妻子倚在我身边早哭出了声。远离上海,离别家乡的村庄,我和妻子在海南岛工作和生活。我和妻子双方的爹娘都已经六十开外的年纪,我们在外地打拼,有时甚至几年都难得见到父母,要是回到上海工作,总能找点时间,赶回郊区村庄看看老人吧。再说我的儿子读小学四年级,也快认不出他的爸妈了。于是,我与妻子决定,回到上海重新寻找工作,要离父母、儿子近一点。我跟妻子开玩笑说:“果果啊,大不了我买两只碗,去上海大街上自己当‘老板’”。妻子一本正经地说:“亏你想得出,我才不跟你讨饭呢!”
那年春节后,我带着妻子辞职回到了家乡。路过上海,依然繁华美丽。我的村庄呢,楼房是多了几幢,并没有多少装饰,小河浜淌在乡间小道的纵深处,岸边的土墩,村口的老榆树,社场的牛棚,田埂上撤野的狗,这些熟悉的环境像一幅画,在我的眼睛里依次闪过,感觉朴素得毫无脂粉气,从前是这样,我出远门那么多年回来,村庄还是这番景象,我却第一次觉得踏上村庄土地的厚重,这是一种凝重的美,来源于古老的民间生活气息。
不远处,我望见爹娘家的房顶,稍近些,屋檐下有两根长竹竿,晾满了洗净的衣服,有几件蓝嵌条颜色的汗衫、衣裤,应该是儿子的。我的心里很激动,马上要见到在异乡日夜牵挂的儿子和爹娘了。这时,我娘牵着儿子从屋后邻居家出来,我们都看到了,几十米距离,儿子撤腿奔跑,我妻子向前迎上,母子俩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我喊着娘,握着娘的手说:“娘,我和果果回来了,不出远门啦!”娘淌着眼泪说:“好、好,回来就好啊!”我问娘,爹呢?娘说,你爹啊,晓得你跟果果今天回来,兴奋得一直在场心里转悠,吃过午饭拿一把铁铲,干脆去田地看看有什么要做的。我进屋放下行李,直奔张家后院一块责任田,找我爹去了。
●久别重逢,与儿子一拍肩膀,与爹娘一壶酒,我在外省几千个日夜的思念,顷刻融化在血脉亲情中。静下来,我仔细看看爹娘,他们明显老了。我们作为小辈的责任显得更大,除了对爹娘的健康、身心关怀外,应该要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我与妻子商量,先把爹娘名下的责任田租给人家养蟹,有一份租金收入,同时减少老人家风吹日晒出门种田,宅前自留地种点新鲜蔬菜,当作健康锻炼。我爹第一个不同意,他说身子骨还硬朗,大半辈子泥土里刨食,过清闲日子,不闲出病来?娘瞧一眼我儿子,说,孙子大了,你们也回来了,这几亩田地还是留着自己种,不用花多少力气,稻谷撒下去就完事,稻熟了,有收割机上门服务,算算收成,一熟稻就顶全年租金。我听爹娘的意思,最主要是田地租出去不合算,那时农业税国家取消了,种水稻另有政府补贴,不种地算什么农民。爹娘这种想法,我想可能代表许多老一辈农民,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在村庄种田,拼着命考上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即便考不上大学,也要去城里开出租车或打工,他们认为头上这顶农民帽子太土,在工厂干上几个月,工资比种一年田来得容易,说出去面子上也好听。
说到这个份上,我妻子表态说,既然爹娘闲不住,还为我们小辈操劳,田地暂时不出租。过几日,我和费新要到市区打算接手一个小厂,等事情定下来,厂子里需要人手,爹娘可以来厂里帮一把,到时再把田地租出去吧。我娘一听,她说不行啊。我知道娘最远去过一趟县城,那是没有办法才去的。年轻时,有一次娘出工摘棉花,突然嘴里感觉有股腥味,张口一吐,竟是满口鲜血,接着就昏迷,跌倒棉花地。被社员发现急送小镇医院,院方医术条件有限,要求我娘转去县城中心医院救治。县医院诊断,我娘患大出血疾病,动了大手术,被切割了三分之二的胃。出院回家的路上,搭了一辆车,赶百里路,晕车吐了一路,差点又丢半条命。我娘说,再也不坐车,不出远门了。此后,我娘胃小了,她的饭量就那么一小碗,幸运的是,直至耄耋之年,我娘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后话。
●上海这家电器厂,转让给我时,起初仅仅是小规模经营,为外地加工一些电器配件,一旦定单少,或者质量不合格,无法接定单,有很大的投资风险。我在海南十多年时间,确实学到不少技术、管理方面的经验,尤其是与各类人员打交道积累的见识、闯劲和胆量,自己感到一个小厂还是能够驾驭,再说这些年在经济上毕竟有些底子。
在设备、工艺上,我先进行改造,同时聘请高级工程师进行技术创新。在产品销售上,拓展业务量,力求经销为主,加工为辅。经过几年尝试,有了自主研发的产品,申请了国家专利,对接海外代理商,我的部分产品销售国外。外销这一块,被中间商赚去大头,都是二三手订单,一开始并不赚钱。
不久后,我逐渐摸清行情,懂得其中的门路,特别是结识南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客户。渐渐地,通过邀请外国客户来上海商务旅游和考察,我整天陪同外商去国内销售单位,让他们体会到我厂的产品是规范的,质量过得硬,受到用户欢迎。当然,玩是免不了的,外滩,豫园,上海老饭店,崇明岛森林公园和东滩湿地,朱家角和枫泾古镇,带老外到处走走看看,地方特色小吃、老酒,更是必需的招待。客户是上帝,也是朋友,这是真理。我以诚相待,将自己厂里生产的产品,以最实惠的价格,为供需双方共同创造效益,老外感受到中国人做生意,是交朋友放在第一,正如儒家思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四五年客户资源积累,我的订单越来越多。分析销售形势,我发现外销有一个奇怪现象,先从远的国家,慢慢带动近一些国家,陆续前来洽谈业务,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商人,这些地方比较发达,距离近,我的运行成本低,产品价格高,我的工厂开始赚钱了。
从海南回来,原想常回家看看,但在家门口了,我却忙得没有时间回老家。妻子安慰我说,与爹娘、儿子近了,心里总是踏实的,有事坐船渡江,虽不方便,从市区到村庄三四个小时,毕竟叫得应。路上多花点时间,我还可以忍受,要是碰到雾霾天气,或台风、强对流,客轮停航,一江之隔,那真叫两眼一抹黑,找不着方向。为照顾爹娘,减少负担,我开厂第二年,把儿子迁到市区学校念书,与我们一起住。我动员过几次,叫爹娘到市区居住,省得我和妻子来回跑,再说我厂里有一百多员工,不在意多开老两口一份工资,不用工作,在身边图个放心。我爹还是不愿意,说是有力气,工厂活做不来,在村庄里接地气,待惯了,种田地,吃用开销不愁,反而劝我和妻子果果省点钱,开厂寻钞票不容易。我娘与爹一个口气,说城里人多,车多,闹哄哄哪里睡得着觉,吃的东西又不新鲜,就在村庄里为我们种蔬菜,养些鸡鸭,总归比市场买的好。爹娘啊,一辈子不想麻烦自己的儿子、媳妇,包括邻里乡亲,还说这是做人的规矩。果果两手一摊,跟我说:“怎么办?老两口犟牛一对。”我对妻子说:“就顺着爹娘吧!我们只好抽空多回家看看。”
做企业,随时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多次历经金融风暴的考验,一次次化解挺过来了。爹娘听到社会上传的一些风声,就会打电话劝慰一番,叫我不要急,也不用怕,家里还有几亩责任田,饿不死人。这时,我知道老人家虽不懂工厂,但时时为我担着一颗心,就像在田埂上挑着一担百余斤稻捆,一不小心会摔倒。快到冬天了,我娘惦记着被子破旧,薄了,早早的去小镇轧棉花工场,新弹几床棉被,托亲戚带到城里。我回家,爹忙着做一桌好饭、一壶好酒。离开村庄回城时,娘早准备了一筐新鲜蔬菜,果品,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妻子每次给我娘捎点钱,当面给,娘不要,于是悄悄地把钱放在我娘睡觉的枕头里,到了城里告诉娘一声。娘嗔怪着,给我钱干啥,又花不掉。我和妻子开心地笑,娘终于肯收下了。我们就一次次给,放衣柜、布包、床单下、茶几搁板上,心里有了安慰。而娘一次次攒着,到了春节,放在红包里,额外另加一笔钱,全部给我儿子做压岁钱。唉,我和妻子都对爹娘没有办法,心里感激着,同时激励着我们好好做人。
●到了2009年,总算盼来长江隧桥开通,登陆点就是我老家陈家镇。这样我从市区回村庄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往往在周末,我带上妻子和儿子,回爹娘家吃晚饭,把爹娘乐得每星期盼周末快点到来。不过呢,刚形成周末团聚这个格局,第二年,老家房子要拆迁。爹娘愁了,房子拆掉,意味着田地没有了,七八十岁年纪还想着种田这事,我真佩服父母辈这一代农民,他们才是全心全意为土地服务的老百姓。拆迁对于这个农民阶层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转折。
我想这回爹娘没话说了,应该乖乖的跟我到市区居住。然而,不容我开口,爹娘已经与一帮老邻居商量好,一起租房子到未拆迁的乡亲们家住下,仍然做邻居,等待政府提供安置新房子。签拆迁协议时,告知两老拿新房子,我与妻子乐观地想,暂时租借小房子过渡,就等两年吧。
谁晓得到了2014年,据说新房子还没建造竣工,而我爹娘的年岁更大了,我的心里笼罩着一丝忧愁,拆迁好多年,他们这个年纪还住不上自己家的房子。那年母亲节来临之际,我写了一首《妈妈》的诗:老屋承载几代人甜酸苦辣/所有远足都从这里开始/脚步踩出一段段光阴/守护乡野阡陌花开花落/无需过多语言/妈妈住着/指引我回家的方向/故乡是一袭暖身的棉衣/我最喜欢老屋居住的日子/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宅子被拆迁队推倒/你乐观表情留不住涌出眼眶的泪水/我懂得你心中有千万种不舍/你从来没有用过一支口红去过一次上海/当台风把小屋一角吹倒/你扑进风雨中砍来一捆芦苇几根树杆/重新垒实的小屋儿女们不再惊恐/你满脸雨水泥巴却是那样美丽/社区工地房子在一层层垒高/同时垒高你满头银丝的年纪/可你逢人就唠叨明年搬新房/一说四年还是借住乡亲家/生活把你耳朵磨钝了/每一句话不知自己能否听见/我唤妈妈总要凑近你的耳旁/卑微的日子里常说不缺什么/在梦境中依然生长喂养儿女的粮食/有一天傍晚想看看妈妈/想不到你早已睡下/我叩门/爸爸应声的喜悦填满一屋子/妈妈披衣迎一脸笑容皱纹叠现/嘴里念叨怎不早点过来吃饭/享受我们渺小而真实的快乐/妈妈知道我近来右肩膀酸痛/你催我把衣服脱掉/用艾草发丝浸白酒还有一生的爱意/捏成一团要为我的伤痛按摩/要是不听你会伤心睡不好觉/我明显感到你没有从前的力气/你一身劲道将岁月种成庄稼/曾经穿透晚霞炊烟里的声音/再也找不到你年轻模样/妈妈你的一生恩情牵挂/我何以回报感谢你的体面和尊严/今夜我拿起搁置久远的诗笔/为你郑重写下诺言/亲爱的妈妈/我永远爱你。落款时间是2014年5月8日夜。
在诗人眼里,这首算不上诗,但我还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真实的情感,也是我从海南回家的动力,而创业仅仅是我人生的一个侧面,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孝易,顺难,如何做到两全其美,的确值得儿女们多想想。爹娘在,是儿女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