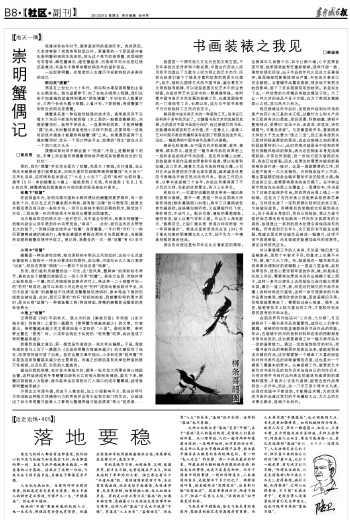每逢深秋初冬时节,通常是崇明的旅游旺季。究其原因,大多游客除了观赏崇明秋景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冲着吃崇明蟹和崇明羊肉来的。因为这个季节的崇明蟹,肉质细密而有香味,雌性蟹黄足,雄性蟹脂多;而崇明羊肉无论是红烧还是煮汤,均是冬令御寒助暖抗病延年的滋补佳品。
一说起崇明蟹,在笔者的人生履历中却能钩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明沟里“摸蟹”
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明沟和水渠是崇明蟹的主要生长栖息地。每当盛夏季节,知了在枝头唱得人烦躁,我们这些不知疲倦的顽童特别喜欢“捞鱼摸蟹”:午间在农人歇夏时分,三两个伙伴头戴小草帽,上着汗衫,下穿短裤,身背蟹篓下到附近的明沟里摸蟹。
摸蟹其实是一种经验性较强的技术活,通常是用双手沿着水下沟沿不断地向前探摸(水上面的一般都是蟛蜞洞),当摸到蟹洞时,就将手伸进去,一直要伸到洞底,才能将螃蟹“摸”出来。有时蟹洞深或者狭小手探不到底,还要采取一些耗时的技术措施才能最终将螃蟹“摸”上来。如果遇到是两个互通的蟹洞时,你从一个洞口伸进手去,狡猾的“洞主”就会从另一个洞口逃之夭夭……
摸蟹回家时双手都会留下“伤痕”:手指上是蟹刺留下的伤,手臂上则会留有伸摸蟹洞时给芦根或其他硬物划出的“红杠杠”……
那时,我们“摸蟹”并非完全是为了吃蟹,而是为了换钱。次日清晨,当公鸡尚未破晓时我们就要起床,用隔天搓好的细稻草绳将螃蟹按“先大后小”次序扎成串,这样倒拎起来就成了“大在上小在下”,这样“卖相”比较好看。通常10只一串的螃蟹在小镇上一般能卖到2毛钱,有时贱卖1毛8、1毛6的也有,螃蟹换钱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夜幕下“找蟹”
在我孩童年代,崇明沟渠河道和水稻田埂处的螃蟹洞星罗棋布,而一到金秋十月,农民在正式开镰收割水稻前,都有做“边障”的习惯程序,就是在水稻田埂四周开挖一条排水沟,一则可以排掉水稻田后期的积水,降低地下水位;二则田埂一年四季经雨水冲刷后也需要加固增宽。
当水稻田四周的排水沟一经开挖后,沟中就会有积水,而喜水的螃蟹一到晚间就会从洞中爬到排水沟里觅食、“乘凉”……此时,我们这些在乡野里长大的孩子,一到晚间就会结伴去“找蟹”:身背蟹篓,一手打着“洋灯”(一种四面镶着玻璃的煤油灯),高卷起裤腿赤着脚在那排水沟里蹚着走,当脚踩到或碰到螃蟹后便伸手捉之。曾记得,我最多的一次一晚“找蟹”有50多只……
小河中“吊蟹”
螃蟹是一种回游性动物,每当深秋初冬季西北风刮起时,这些小生灵就会像接到上级指令一样会沿着来时的路径,由沟渠、河道向长江入海口爬游“回家”,然后在那里“殉情”——繁衍子孙后自我“海葬”。
然而,我们就利用螃蟹的这一习性,在“西风爽、蟹脚痒”的深秋初冬季节,喜欢在处于螃蟹回游路径之一的小河里“钓蟹”。具体方法是:用铁丝穿上蚯蚓弯成一个圈,然后用粗线将其牵在芦竹上,将这种一二十根整齐划一的“钓杆”制成后,就可以来到小河边将这些“钓杆”成排地垂放到河中央,当河中回游“返家”的螃蟹经不住诱惑用蟹螯钳吃诱饵时,原本弯曲下垂的钓线就会被拉直,此时,我们只要把“钓杆”轻轻地抬起,到螃蟹即将钓离水面时,即用长柄“盆操”(一种捕鱼蟹工具)将其捞起,馋嘴的螃蟹即成餐桌的美味佳肴也……
小报上“说蟹”
记得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从当时的《解放日报》市郊版(《东方城乡报》的前身)上看到一篇题为《崇明蟹为啥越来越少》的文章,作者提出,崇明蟹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是小龙虾的“入侵”。据他观察,崇明野生蟹在“脱壳”时,小龙虾会将处于劣势的“软壳蟹”吃掉,因此造成了崇明蟹越来越少……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第一感觉是作者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于是,我就有感而发马上写了一篇题为《也谈崇明蟹为啥越来越少》的文章投到了报社,结果很快就刊登了出来。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小龙虾吃掉“软壳蟹”并非是造成崇明蟹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有关单位野蛮的毁灭性捕捞,以及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
据当时我的观察,在许多水闸放水时,都有一张尼龙大网罩在闸口捕捉鱼蟹,这样就造成秋冬季螃蟹回游到长江时被无限制地捕获,数年下来,螃蟹回游链被人为阻断,每年能幸运回游到长江入海口的成年蟹骤减,就导致崇明蟹越来越少……
尽管此文有理有据,但由于人微言轻,加上小报影响不大,我当时呼吁尽快消除这种毁灭性捕捞行为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以致造成了如今崇明蟹只能靠人工繁育与蟹塘养殖才能延续其“香火”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