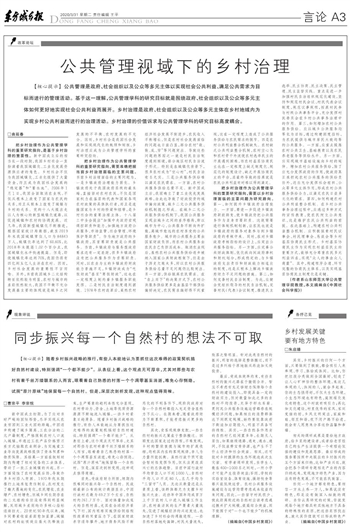□曹宗平 李宗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尽早实现从农业穷国到工业大国的跨越,中国逐步构建了城乡隔离、工农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抽取农业剩余,为实施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提供了资本积累和物质保障。其结果一方面在较短时期内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带动了一批工业城镇的兴起,另一方面侵蚀了农村发展后劲,导致许多乡村陷入贫困。1970年代末期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增色,但城乡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非但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反而城乡差别的许多核心指标逐渐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间要素收益差距愈加显著,城镇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生产要素的趋利本性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镇,一些乡村景象日趋萧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有些人本能地认为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政策契机搞好自然村建设,特别强调“一个都不能少”。从表征上看,这个观点无可厚非,尤其对那些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而言,眼看着自己熟悉的村落一个个凋零甚至消逝,难免心存恻隐,试图“原汁原味”地保留每一个自然村。但是,深层次剖析发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受政府财力所限,短期内很难同时振兴每一个自然村。民政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行政村总数为69.2万个左右、自然村约261.7万个。面对体量如此庞大的自然村落,尤其在全球经济景气下行、国内艰难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压力下,在国家财政赤字逐年攀升、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恶化的不利条件下,现阶段政府对每一个自然村都投入充足资金显然力不从心。长期来看,随着政府财力不断累积,才能考虑振兴更多的自然村。
其次,受客观规律支配,一些自然村的振兴之策在于整体搬迁。回顾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乡村的繁荣衰微与城市的扩展收缩,均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非人为力量所能抗衡。虽然行政干预可能会暂时性发挥作用,但无法更改其兴亡的总体趋势。目前中国行政村平均常住人口不到1000人,自然村平均人口不足80人,且几乎均为“三留守”人员。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素质上看,该群体都无力支撑乡村振兴大业。近些年中国年均成百万上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农村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失,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兴旺发达,也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凋敝进程。一些自然村落地处偏僻,村民大量流失,败落之势明显。针对此类自然村的振兴,明智的选择是整体搬迁,而不是过多纠结于原地振兴再追加无效投资。
最后,受成本效率约束,有些自然村的振兴之路在于撤销合并。暂且不考虑有无足够财力保障每个自然村的建设投入,即使具备一定的财政实力,但对数量如此之多的自然村平均投资,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何况公共服务设施运营都存在规模经济问题,如果相应的消费群体达不到既定规模,始终要依靠政府不断追加后期投入,明显不具备可持续性。其实,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自然村已经闲置多年,长期无人居住,如果继续通路、通电、通水、通网,不仅浪费宝贵资源,也产生不了什么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反,还可能对乡村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次生灾害。有学者调研发现,当学生人数在400-1000名之间时,一所小学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否则,学校的实验室设备、体育设施、操场校舍等都只能低效运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运营均需考虑成本收益约束问题,因此,一些留守村民很少、彼此距离较近的自然村应该考虑通过撤并扩大规模,提高综合效益,而不能囿于对“一个也不能少”的机械理解。
(摘编自《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