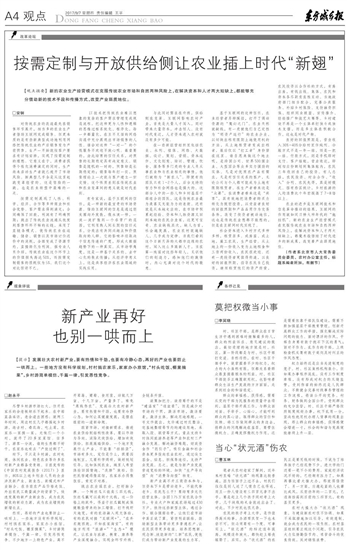□安钢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最先在销售环节展开,相当多的农业生产者借助互联网完成销售。但更本质的是有些新典型成功地利用网络把传统农业的产后销售变为产前预售,生产一开始就按客户要求有计划安排,实现了按需定制的理想。它意义在于,消费者获得个性化消费满足的同时,生产尚未启动生产者就已避开了市场风险。新典型几乎全是从这里起跳变革经营的。这是惊险的一跳,也是农业转型中最难的一关。
按需定制展现了人性、科学、经济、合作等多种商业和社会优势。客户需求得到满足;合同确保了回款,利润有了明确预期;跳出了传统农业流通从批发到零售环环不畅的长链,采用了直链条模式。使传统农业在运输、储存、销售以及市场讨价还价中的消耗,全部变成了资源节约,直接转化为利润。据专业人员介绍,传统农业在这个环节上的价值损失高达50%,而按需定制销售的损耗仅为5%。我们这个对比惊讶不已。
IT技术把传统农业难以想象的复杂的客户需求管理变成规范流程,把这种更为人性和逻辑的思维过程系统化、程序化,每一步都量化,在互不见面的网络沟通中充分展现出市场销售的人性。谁会对这种“一对一”的个性服务不欢迎不放心呢。最重要的,由此培育的信任关系,对预售的长期稳定具有决定意义。销售是随机的一时的,预售却是长期稳定的;销售每年打一仗,预售理论上一次就与客户建立一世交情。这个性质差别在传统农业和农业变革间的意义就是时代差别。
有专家说,基于互联网的信任,是一种新的最宝贵的市场资源。借助互联网的信息是通过朋友圈向外发散,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扩散到一个非常广的范围,它利用熟人间长期的信任关系,分类出有共同兴趣点和价值取向的人群。它的影响半径取决于信息传递的广度,形成大数据趋势下的一种真实。从市场学角度,这是一种基于关系的、去中心化的散点传播;从经济学意义上,这是共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实践应用。
与此同时需求在升级,供给侧在变革。互联网影响农村产业,首先是大量人才闯入,同时带来大量资本,冲击惊人。没有时代变迁,人才资本进入农村就没有多少可能。
在一些新经营组织里包括农业、水利、植保、网络、大数据、设计、策划、营销、资本运作、文化创意、培训、管理、饮食、服务等多门类的专业人员从事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事情,他们被称为“新农人”。即便有的团队只有1~2个人,后台支持的智力和社会网络也是强大的。这部分人中的一些人和乡村基层干部组合的团队,这是传统农业最为羡慕又无能为力的差距。还有就是从本地走出的,在市场中积累起经验、资本和人脉资源又回到本地的农民企业家,这更可宝贵。农业缺钱其次,缺人为首,社会越发展,农业农村就越缺人,几乎成为定律。当我们看到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边缘的农村,闯入这么多高新人才,当在第一线面对这些年轻人,见识他们的创造力,感知他们的激情时,内心充满对这个时代的敬意。
基于互联网的这种信任,农业经营者另辟蹊径,打开了调动资源的“魔幻之门”。农业天然就缺钱,有一类被他们自己定性为“轻资产运行”的农业企业,以切块出租有限期土地使用权的方法,从土地租赁者变成出租者,最后仅以“打工者”身份留在这里。谁自愿来做这个地主呢,是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等众多实力强劲的实体。凡是对优质农产品有需求,凡是有信任关系的客户,无论公司与个人都可能成为土地有限期租赁者。在生产者看来这是“众筹”,在消费者看来这是“共享”,其有效地把消费者购买力转化为提前投资,以受益者良好的回报预期和产品品质作为交易条件,改变了投资者被动地位,这也是传统农业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
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方式多种多样,租赁居多。或房屋、或土地,雇工农民,生产经营。从土地上的一份收入变为土地租金和工资两份收入,农民很欢迎。还有一类投资者更值得称道,以良好的回报预期,指导农民自己投资,继而租赁他们的资产经营,农民投资以合作社的方式,有房出房,有钱出钱。集体、农民和资本各尽职责良性互动。当地政府部门相当配合,完善公共服务、补贴乡村保险、支持融资担保、组织同业联盟、宣传推介、经验推广和技艺大赛等。乡村建设不再是一个主体单打独斗或独木支撑,而是多主体在积极合作,这也是时代产物。
良好的回报预期是,营业收入30%~40%分给村里作纯利。分账方式不是一年一结,而是一把一结。付款方式,则是手机即时支付。客户结账,营业收讫,即刻相应份额划到集体账内,农民三年收回自己的投资。有人总结,农民投资、村企合作、“收入”分利、农民先得,真是好模式。据有些区统计,乡村旅游的人均消费比十年前提高了7~8倍以上。
农业的进步是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推动的结果,互联网的作用就如同刀耕火种年代的“拖拉机”。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在克服传统农业市场和自然两种风险上,在解决资本和人才两大短缺上,都魔术般借助了时代进步的新成果,改变着产业弱质地位。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农村办公室主任,标题系编者所加,有删节)